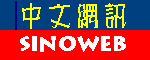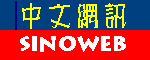|
■“司法公正”四人谈
(其四) 律师说:要“对抗”,不要“对立”
--访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律师
●本站记者 贾双林
(回第一篇)
记者:今年是我国律师制度恢复二十周年,您从事律师工作也近十五年了。那么,从自身的感受而言,您怎么评价这二十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状况和司法体制方面发生的变化?
田文昌:可以说,这二十年,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在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过程中,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立法的不断完善。但经过司法程序的实际运作和律师对诉讼的广泛参与,这二十年来,我国的司法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朝着“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向,坚实迈进。所有这些,都是必须加以肯定的。当然,目前的司法体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解决不好,将对我们实现司法公正目标带来消极的影响。
记者:从一个律师的角度来看,您认为目前的司法体制有哪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田文昌:最突出的,是审判独立问题。审判独立是法制建设完善化的最佳体现。我国宪法也明文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这一宪法原则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切实遵守。多年来,一些部门干预、社会团体干预,甚至个人干预,一直难以消除。
之所以如此,除了个别人滥用权力外,我们中国人在意识上远未摆脱“人治”时代思维模式,也是一个主要因素。就拿案件当事人来说,在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他会激烈反对“干预”;而当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他又去千方百计托关系、找门子,希望有大人物来“干预”。
另一个让律师比较头疼的问题,是地方保护主义加剧和上级司法机关权威弱化。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今年5月,我代理了某地一个案子,原定6月初开庭。因我5月底要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一个国际会议,希望能推迟开庭。我在向该地法院提出申请的同时,也向最高人民法院说明了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也向该法院发了正式的工作函,要求该法院推迟开庭。但该法院回函最高人民法院,居然说田某人不是该案的代理人,还捏造日期说如不马上开庭,就要超审限。最高人民法院在调查的基础上,又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函,要求该法院立即同意推迟开庭的请求。而最后的结果,真可谓悲哀!该法院回函说,经请示本地政法委同意,该案将于6月1日开庭,不再变更。
这样的事,几乎每个律师都遇到过。这里反映出的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我的看法与其他一些学者大致相同,必须采取“垂直领导”的体制。而且,作为律师,我更呼吁尽快向这个体制转变。
记者:我注意到,随着律师职能的变化和在诉讼中的广泛参与,目前在律师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上,好象存在一定的紧张态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田文昌:从根本上说,这是计划经济和“人治”的残留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的新局面,碰撞后产生出的一种“对立”,一种简单的、带有情绪化的“对立”。
在律师制度恢复初期,大家或许记得,律师也是着制服、配手枪的。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律师是国家司法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执行的也是国家赋予的惩罚犯罪的使命。而大量的民事案件中,根本寻不到律师的影子,替老百姓写诉状的一般是算命先生或退休老干部。在当时,律师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没有这么紧张,也不可能有这么紧张,因为都是一家人嘛。
而随着形势的发展、诉讼法的不断完善和司法体制的不断改进,律师的职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突出的就是,要真正依法为当事人服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律师要充分发挥作用,就肯定与司法机关的一些旧观念、旧体制的残留发生摩擦、碰撞。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好事。这说明法制建设有了成果,而且也会促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但如果老是停留在简单的“对立”上,互相形成一定的成见,那可就不是好事了。
今年我代理的一个地方的刑事案子中,就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开庭审判前,律师单独会见当事人,是完全符合诉讼法规定的。但当我进入看守所的时候,我发现有来自四家单位的人在等着我,公安局的、检察院的、法院的,还有当地纪检委的。我会见的时候,他们就在场听着、看着,还多次打断我与当事人的谈话,态度极其强硬。这是严重违反诉讼法的,也是近年来极为罕见的。其实,这就是一种有成见的和不信任的情绪化“对立”。
我不否认,律师在有些方面也有不妥之处,律师队伍中也有害群之马。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具体的人,不论是司法人员,还是律师,而在于体制,在于良好体制下合乎理性的一种关系。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合乎理性的关系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田文昌:应该是一种严格在法律框架内的“对抗”与“合作”关系。
这种关系,其本质是严格依据法律,以制约求公正。司法机关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给违法者以制裁,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律师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尽力争取当事人应有的合法权益,并求得公正的司法判决,其实也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所以,在浅层次上,二者是“对抗”;在深层次上,二者是“合作”。
这种“对抗”,与简单的、情绪化的“对立”,有着本质的不同。以法庭上的控辩关系为例:检察官指控被告人,他要摆事实、罗列证据、阐述法律,从而做出被告人有罪的结论;律师为被告人辩护,也要摆事实、罗列证据、阐述法律,从而做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结论。双方可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但目的只有一个,将最清晰的证据和法律关系摆在法庭上,等待法庭的公正判决。这种“对抗”是理性的、智慧的,并且是神圣的法律最富魅力之处。
而一旦陷入“对立”,尤其是律师与司法机关的整体对立,或者说司法机关整体上对律师有偏见,那后果就不堪设想。本来,我们的公、检、法三家,就有“沟通”、“协调”的不良传统,如再联合起来“对付”律师,那案子就没法辩护了。法庭审理就纯粹成了走过场,任你律师口若悬河,判决书恐怕早就拟好了,只待宣判了。
律师并不是社会异己力量,也不是“坏人”的保护伞。在法制发达国家,律师是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和谐的重要力量。虽然,律师曾让辛普森这样的“坏人”(由于警方程序失误)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每一个老百姓还是信任律师、依赖律师,司法机关也没有因此就想方设法去对付或是掣肘律师。因为,从来就没人相信,法官一定是公正的、纯洁的、毫无偏颇的。
记者:在您的一些文章中,您还谈到新闻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作用,能不能简单谈谈?
田文昌:过去,由于我们的新闻媒体官方色彩太浓,“干预”的程度也就大一些。所以,有学者和司法机关反对新闻媒体过多地介入一些个案。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许多媒体的官方色彩弱化了,成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舆情手段。那么,在一些与老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案子上,或是受地方行政权力干预颇多而无法深入的案子上,通过新闻媒体予以公开披露,在老百姓的注视下,使案子得到公正的处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新闻监督当然也有负面的一些效果,但权衡利弊,我认为,利大于弊。这是对司法监督体制的一个重要补充。
田文昌,法学硕士,副教授,曾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85年起从事律师工作,先后成功代理了大邱庄被害人控告禹作敏案、81名乘客诉西北航空官司误机索赔集团诉讼案等重大、疑难案件,1996年被评为北京市首届十佳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