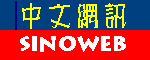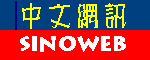|
■“司法公正”四人谈
(其一)
建立以法律家为中心的司法体制
—访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贺卫方
●本站记者 贾双林
(下一篇)
记者:国内读者注意到,近年来,您就司法公正和司法体制改革问题,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我想知道,是什么促使您在这方面又投入了较大的精力,去进行一些研究?
贺卫方:其实,我对司法体制问题一直是比较关注的。八十年代初期,我走上学术道路的第一篇文章恰恰是研究英国陪审制度的。其后,虽然学术兴趣略有转移,但从未间断过对司法体制问题的研究。我之所以如此重视司法体制问题,来源于我对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有了好的法律,并不意味着就必然带来好的法律秩序,而要真正实现好的法律秩序,就必须有一个以法律家为核心的司法体制。
近年来,我又比较多地关注中国的司法体制问题,是由两个方面的现实因素促使的。其一是有感于我们的立法越来越完备,而司法却越来越混乱。司法中的不公正和司法腐败问题日益凸显,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这说明,一定是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二是有感于国内的法学研究存在脱离社会生活的现象,由于学科划分的局限,许多很现实的问题被遮蔽了。比如,司法体制问题,就研究得很不够。
记者:您刚才讲到“以法律家为核心的司法体制”,请您简单谈谈这种法律思想的具体特征。
贺卫方:简单来说,就是指司法体制的核心是法官,具有极大的权威;而法官又必须是具有较高素养的法律专家。法官必须受过严格的法律教育和司法实践训练,必须经过严格的选任程序走上工作岗位,必须受严格的司法伦理(Judicial ethics)约束其行为。事实上,在世界上法制发达的国家,最好的法学家就是法官。其不光是在司法过程中的地位尊崇无比,而且还是法律学说上的权威。
记者:我注意到,在您的许多文章中和今天的谈话中,谈到司法体制,具体说是谈到司法人员时,更多的是以法官为主要表述对象的,那么,在您看来,是不是只有法官才算司法人员呢?
贺卫方: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只有法官才是真正的司法人员。检察官其实是以行政方式执行法律的准司法人员。而警察,属于行政机关,并不是司法人员。所以,我这里谈的司法体制问题,主要是以法院和法官的运行体制为主,也涉及到检察院和检察官。
记者:就您的观察和研究,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司法体制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司法中的不公正又有何表现?
贺卫方:首先是司法体系从属于行政体系,以致于“司法独立”成为一句空话。在我们的地方法院、检察院那里,人事上的任免归地方人大,经费来源是地方财政局,甚至很多地方是由公安局长任政法委书记来领导和协调公、检、法三家。汉密尔顿说过:“对一个人的生存有控制权,就等于对一个人的意志有控制权。”这句话对我们的司法机关其实也是适用的。造成的后果是,不光独立办案、公正办案受到严重干扰,还形成积重难返的地方保护主义。在有些地方,司法机关“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居然成了优秀业绩的代名词。又比如,在一些经济案件中,审理和判决明显倾向本地当事人。给人形成的印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院成了当地人的法院。
其次是法律的执行规范缺乏统一和详尽的标准,以致于法院和法官个人的随意性太大。全国性的司法解释目前仍处在滞后、粗疏和零散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会出现一些适用法律不当和判决不公的现象。比如,遇到某些关系到不同地方利益而涉案金额又比较高的案件,不同地方的法院便“不辞劳苦”地争夺案件的管辖权。试想,如果又严格、明晰的管辖权界定规范,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而且,这种标准上的混乱也为司法腐败准备了足够的活动空间。
再有就是司法机关的自我运行机制上存在着严重的行政化、官僚化现象。司法机关不同于行政机关,其上下级的职权划分、司法人员的选任、内部的管理机制等各个方面,应有其许多的特殊之处。而在我国,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这种运行机制上,并没有太大的分别。比如,人事制度和司法人员的选任,仍然采取的是类同于干部调任和公务员录用的方式。比如,最近有一个地区的县级法院院长换届结束,大家发现这些院长几乎全是从乡镇长的岗位上“调任”过来的。还有,“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集体”、“民主集中制”等行政机关的组织原则,也照样适用在司法机关。这些方面的错位,容易造成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的“工具化”倾向,不能正常和严格地依法办案,对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也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缺乏一种严格的司法伦理来约束法官的行为。从法制史的研究中,我发现,最能有效地杜绝和控制司法中的暗箱操作及司法腐败的,不是一些空泛的思想道德说教和组织纪律条文,而是适合其行业自身规律的,严格、明晰和翔实的伦理准则。而在中国,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却恰恰是这些“泛道德”的概念和组织原则上的各类要求。比如,“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等。又比如以前曾极为盛行的提法,就是法官的“五不怕”:不怕罢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这些带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号召,出发点是好的,但在现实中,又有多大的约束力呢?
记者:记得去年您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谈及大量的军队转业干部进入司法机关,给司法人员的素质和办案质量等带来的负面影响,曾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和指摘,当然也有不少人支持您的观点。现在,您还坚持自己的观点吗?
贺卫方:是的,我还坚持我的观点。事实上,这是活生生的现实,只不过有些人不愿正视罢了。另外,我想补充的是,要司法机关完全不接收军队转业干部似不太现实,那么,接收可以,但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教育和司法实践训练才能走上工作岗位,必须达到《法官法》明文规定的最起码的要求,即经过大学法学教育或从事司法工作两年以上。
记者: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您认为我国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应从哪些方面去着手呢?
贺卫方:首先应解决司法体系从属于行政体系的问题。这需要人、财、物等这些最根本的体制上去动刀,彻底理顺二者的关系。这其实不光是一个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了,而是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再有就是应注意到司法区划并不等同于行政区划,我们要检讨一下,是否有必要严格按照行政区划逐级设立那么多的地方各级法院。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取消省级分行,设立大区分行的做法,或许对我们的司法体制改革是一个启示。
其次,要尽快改变我们在法官、检察官选任标准上的混乱现象,这个问题是相当迫切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已经相继颁布实施,而在许多地方,仍然是以组织原则代替法律规定、以公务员的标准去套法官、检察官的标准。这一状况必须改变,一定要严格按业已颁布的法律执行。同时还应建立起适合司法机关自身规律的、具体详尽的选任及其配套制度,真正把一批对法律有较深理解的人选任到法官、检察官的位置上。虽然我们离“以法律家为核心的司法体制”还比较遥远,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再有,要注意理顺司法机关内部运行机制上的各种关系,要有一整套相关的制度出台。用这些制度来更严格地规范法院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限定法院院长的职权范围、庭长的职权范围、审判长的职权范围以及审判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等等。
记者:对于如何防止司法腐败,您有什么看法?
贺卫方:长期以来,我们比较强调社会监督对防止司法腐败的作用。这确实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认为并不是最关键的。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最有效的其实是法官等司法从业人员的司法伦理,俗话说就是他们的“行规”。有了一种明确、详尽、严格的司法伦理,法官司法程序中每走一步,都可预期他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而如果他的选择是搞暗箱操作或司法腐败,恰恰这种行规又告诉他,这样做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那么,他就认为这种选择是高风险的,就不会去这样做。另外,在严格选任法官的同时,必须提高法官的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和其物质待遇,使其成为一个崇高、神圣而又能给人带来荣耀感的职业。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虽有物质收益但高风险的司法腐败,他就更不会、也没必要去选择它。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主要从事法律史、比较法和法律文化研究,曾任《比较法研究》、《公共论丛》等书刊编委。贺先生对司法体制问题也比较关注,近年来,有多篇文章见诸海内外报纸、期刊,均引起了较大反响。 |